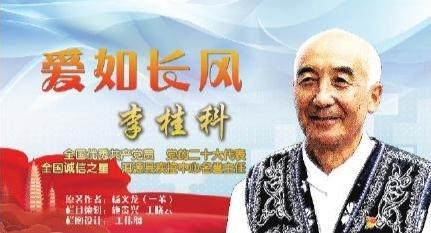古老的中国对麻风的认识与西方不同。秦汉主“风”说;隋唐时有“虫”说;南宋陈言的《三因极——病证方论》(公元1174年)中,除提及外部原因外,首次记述“然亦有感染者”。明代沈之问《解围元薮》中,把传染作为麻风的主要原因,且肯定麻风是可以感染他人造成流行的传染病,并强调了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。明末吴有性(公元1642年)在《瘟疫论》中,将“瘟疫”与其他热性病分开,第一次建立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,感染疠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。清代吴谦等(1739—1742)编修的《医宗金鉴》中,稳固地接受传染为麻风病因之一的观念。
数千年以来,人们就与麻风抗衡,并试图治愈这种恶疾。
隔离,成为自古以来预防麻风传染的主要手段。在《圣经·旧约》中,发现疑似麻风患者,先禁闭七天,确诊则宣布此人不洁,移居城外,与家人及居民“村外隔离”。在公元九世纪的法国,规定麻风患者不许结婚。荷兰、西班牙、挪威、美国及日本等多国,都颁布了麻风患者要入院终身隔离的法令。君士坦丁大帝之母Helena创立救济老人和贫民的“旅社”(拉丁文Hospitlia,为英文Hospital的渊源)。公元329—379年,卡巴多喜阿(Coppodocia)地方的大主教Bacil创建了Bacil旅社,也收容麻风患者。公元四世纪时,欧洲各国共有麻风收容所(隔离病所)636处。十三世纪时,麻风收容所高达19000多处,其中仅法国即有2000处,英国有326处。公元1400—1410年,挪威的卑尔根建立了圣约尔根麻风病院,1702年,挪威基督教会重建。1839年以后,该院成为挪威制定麻风防治对策的本部,也是当时欧洲麻风科学研究的中心。Danielssen和汉森等著名医学家,曾在这个麻风病院担任过院长。十九世纪中叶之后,建立麻风病院收治麻风患者,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隔离措施。1930年,《麻风评论》在英国出版。1931年,国际麻风协会(ILA)在马尼拉成立。1933年,《国际麻风杂志》在美国出版。1943年,在大洋洲的瑞鲁岛,曾发生过岛上所有麻风患者被集中于一艘船上,并用炮火击沉的事件,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悲剧。
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,方才将麻风病攻克。十九世纪前后,采用过大风子制剂治疗麻风。这是七百多年来,唯一可用于治疗麻风的药物,但仅有部分疗效。1897年,首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,决议成立国际性的麻风防治团体,仿效挪威的经验强制隔离患者。1909年,第二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卑尔根举行,仍推荐隔离麻风患者和强制报告新病人。并认为,只有做了输精管切除术后的患者才允许结婚。1938年,在开罗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麻风大会上,埃及提供了大风子树的种子,这是许多世纪以来治疗麻风的唯一药物。1941年,美国麻风患者Stein在卡维尔国立麻风病院创办了《The Star》杂志,并编辑出版至今。
1943年Faget报道,已用砜类药物普洛明(Promin)静脉注射治疗麻风。1943年砜类药物问世,麻风进入了化学治疗时代,使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麻风成了“可治之症”。
1946年至1947年,英国科克伦(Cochrane)医生使用氨苯砜(DDS)肌注和口服治疗麻风。砜类药物治疗麻风是对长期缺乏有效药物局面的首次突破,同时进入化学治疗划时代的新阶段。DDS多年来一直成为主要的抗麻风药。
1948年4月,第五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,主张“只隔离有传染性的患者,可允许部分患者在适当管理下接受门诊治疗”。这次会议中,中国山东齐鲁医科大学尤家骏教授代表中国出席。
1950年,第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报告中,WHO秘书长首次提及麻风病。
1953年,在马德里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麻风大会上指出:“化学治疗的进展,为重新审查本地预防隔离方法创造了新前提”。1958年,第七届国际麻风大会在东京举行,此次会议认为,将患者隔离入院作为控制传染的政策和方法具有重大缺点,“强制隔离是不合时代的错误,应予废除,仅在有特别指征时,才需入院治疗。”同年,WHO(世卫组织)又在日内瓦建立了麻风科。1966年,国际抗麻风协会联合会在瑞士伯尔尼成立。
中国的麻风治疗,可谓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,经历过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。
公元前359—217年的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的《法律答问》中,有秦代将犯罪的麻风患者遣送专门的“疠所”,“生定杀水中”的记载。汉代以后,不许麻风患者参与祭祀和宗社活动,要“绝乎庆吊”或“幽隐山谷”。北齐天宝7—10年(公元556—559年),北印度来华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在河南汲郡霖落山香泉寺中,设立有“疠人坊”,男女分开收养麻风患者,四时供给,可能是中国最早的“麻风院”。晋代葛洪著《抱朴子》中,记有“上党赵瞿,病癫历年垂死,其家弃之,送置山穴中”。公元6世纪末,吐蕃三十代赞普仲年德如身患“龙”病(麻风),考虑会影响后代和王族的兴衰,国王决定与王妃秦萨鲁杰一起活着进入墓穴。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诗人卢照邻因患麻风,去官隐居山中,后不堪其苦,投颍水而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