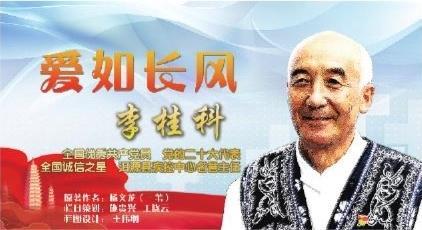胡正清,1961年9月生,主管医师,高中学历,1981年12月参加工作,培训麻风防治专业知识三个月后,开展全县麻风防治。1982年6月到1983年7月,胡正清到大理卫生学校皮防班学习一年获结业证书,1986年在山石屏疗养院为驻院医生,年底回县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。1988年12月,参加云南省麻风联合化疗提高班学习。1990年9月到1991年8月,在昆明医学院学习皮肤病防治,并获专业证书。1994年5月,胡正清参加了广州举办的全国麻风护理研讨班学习,多次参加省州麻风防治短期培训。积极参与麻风科学研究,在麻风防治中作出突出贡献,多次获上级麻风防治先进个人表彰。2016年9月,出席在北京召开的“第十九届国际麻风大会”。
由于疫情期间,胡正清戴着厚厚的N95口罩,说话有些费力。他说:“我们去洋芋山,从县城骑单车到山脚,还要爬山四五个小时。那里主要种洋芋,后边几年产量不行,生存环境恶劣。我们将集中在那里的麻风患者治愈后,便想尽千方百计动员他们的家属让麻风康复者回家,实在回不了家的就安置到山石屏麻风疗养院。有次我们去洋芋山,去的时候是天阴,到那里时,已是雨夹雪,只能待在那里烧洋芋吃,无形中与洋芋山的麻风患者有了更多接触。”
“有时,我们在山下的铺子里买了两包过期的饼干就上山。还有次,我们在山下买了几个饼子,路上饿的时候掰开吃,饼子中间已经拉丝,严重变质。但不吃又饿得慌,我们都是医生,晓得这种变质食品不能吃,但不吃又没别的可吃,只好在路上烧了堆火,用高温消毒的方式烤吃。吃了又不放心,每人又吃了两颗随身携带的利福平。这件事真是终生难忘。”胡正清说。
“李桂科医生在出行经验上确实比我们丰富,出门时候带什么东西,他都会准备。去洋芋山,有三条路可走,可以分别从菜园村、石岩头、白沙河涧上去,为了缓解我们路途上的疲劳,他还一路给我们讲佛光寨古战场的故事。这样说说,那样谝谝。有次我们从洋芋山下来,经白沙河返回,有条沟道跨不过去,李桂科便找来根木头搭在两头,让我们从木头上过,他挨个把我们拉下来。”
“在线索调查过程中,南大坪村报来个疑似病人,我们去看了,反复观察了解,觉得不像,但没有依据。刚好那天我们没带手术包,李桂科医生就批评我们马虎,出门之前,应把该带的用具都带好,似是而非的,必须借助仪器,否则会事倍功半。后来我们又带手术包上去查菌,确诊是真菌感染。”
胡正清聊的都是治疗麻风的往事,但更多的还是与李桂科有关,从中可知洱源县的“麻防”医生们对李桂科的钦佩之情。
许玉梅,1962年7月生,高中学历,主管医师。1981年12月参加工作,培训麻风相关知识三个月后开展全县麻风防治,1982年6月到1983年7月到大理卫生学校皮防班学习一年获结业证书。1983年底开始,她在山石屏疗养院任驻院医生两年,1985年底回卫生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,多次参加省州麻风防治短期培训。在麻风防治过程中,还负责麻风病统计、资料管理、药物管理,并协助王汉喜做麻风杆菌检验,认真负责、积极主动、任劳任怨、勤奋好学、努力钻研、技术精湛,积极参与麻风科学研究,在麻风防治中作出突出贡献,多次获上级麻风防治先进个人表彰。
许玉梅说:“我们在山石屏的时候,每天都要去查菌治疗、割病理组织,同时对家属检查。那个时候没有桥,我们到江边后,坐渡船到疗养院,工作四五个小时,又坐渡船回到健康区。同时,我们还负责炼铁、西山、乔后的联合化疗,每个月都到病人家中发一次药。麻风病的治疗方式虽然单一,却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。家庭破裂、亲朋疏远、社会歧视,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心理问题,也需要我们疏导与治疗。”
许玉梅也提到了麻风病人拒绝治疗的问题。那时采取分片包干的形式,她和王汉喜负责玉湖镇(现茈碧湖镇)和凤羽乡。许玉梅记得,有些病人拒绝治疗,担心自己的病被村里人发现。也有的病人不相信自己得了麻风病。医生耐心和病人解释,是经过查菌和病理检查才确诊的,绝不是毫无根据地上门发药。有些病人听了,经过半年或两年的治疗,彻底治愈。也有的病人坚决拒绝服药,最后落下残疾,追悔莫及。有的病人和医生们成了朋友,他们外出务工,回来都要找她聚聚,聊聊外出务工的见闻感受,聊聊自己的家庭生活。特别是那些已经治愈的女病人,回来也喜欢找许玉梅闲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