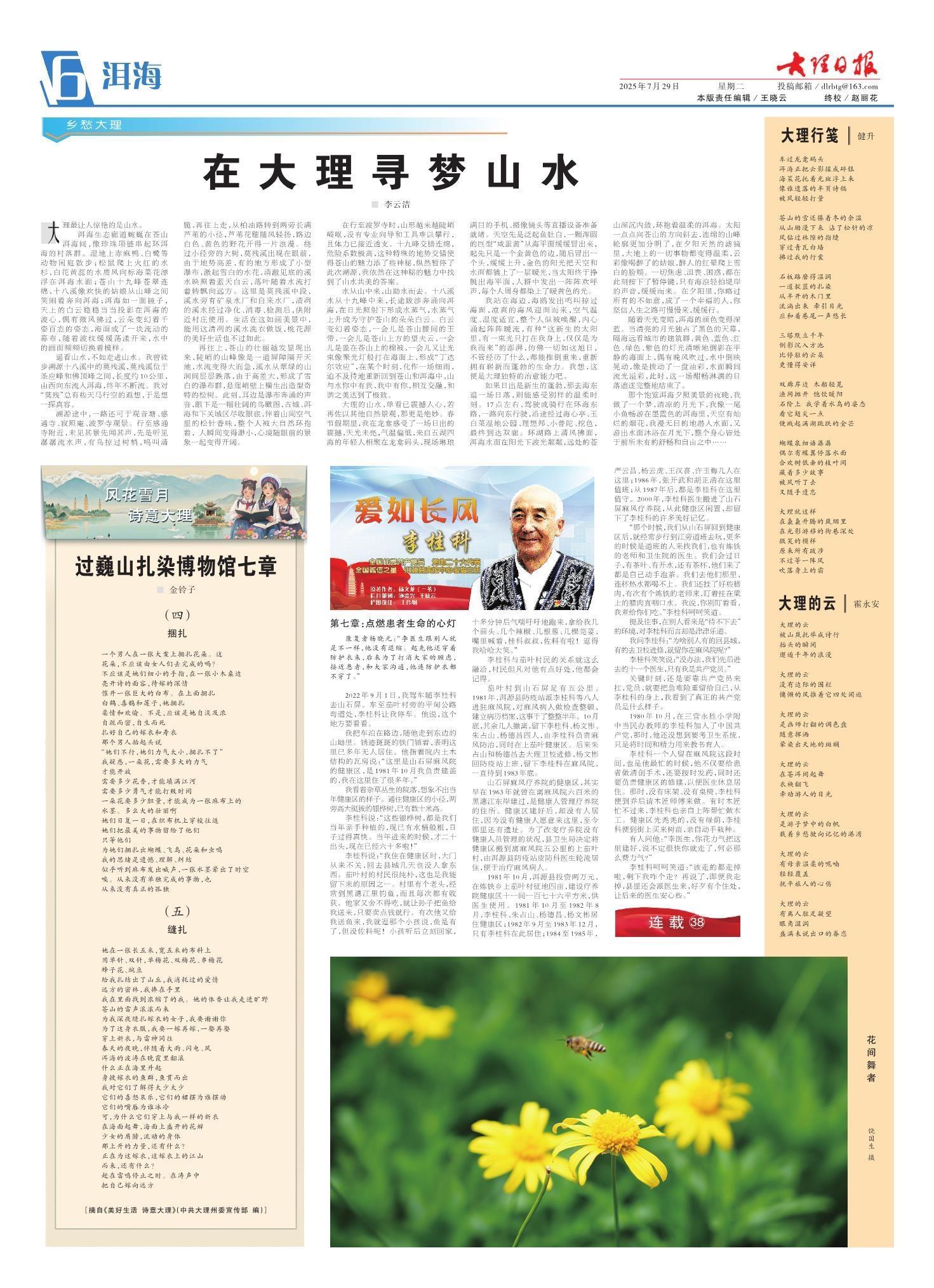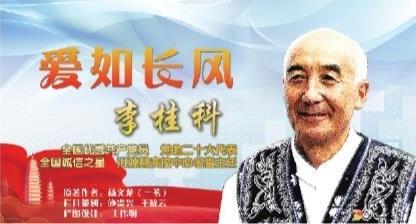第七章:点燃患者生命的心灯
康复者杨晓元:“李医生跟别人就是不一样,他没有退缩。起先他还穿着防护衣来,后来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,接近患者,和大家沟通,他连防护衣都不穿了。”
2022年9月1日,我驾车随李桂科去山石屏。车至茄叶村旁的平甸公路弯道处,李桂科让我停车。他说,这个地方要看看。
我把车泊在路边,随他走到东边的山坳里。锈迹斑斑的铁门锁着,表明这里已多年无人居住。他指着院内土木结构的瓦房说:“这里是山石屏麻风院的健康区,是1981年10月我负责建盖的,我在这里住了很多年。”
我看着杂草丛生的院落,想象不出当年健康区的样子。通往健康区的小径,两旁高大挺拔的银桦树,已有数十米高。
李桂科说:“这些银桦树,都是我们当年亲手种植的,现已有水桶般粗,日子过得真快。当年进来的时候,才二十出头,现在已经六十多啦!”
李桂科说:“我住在健康区时,大门从来不关,回去县城几天也没人拿东西。茄叶村的村民很纯朴,这也是我能留下来的原因之一。村里有个老头,经常到黑潓江里钓鱼,而且每次都有收获。他家又舍不得吃,就让孙子把鱼给我送来,只要卖点钱就行。有次他又给我送鱼来,我就逗那个小孩说,鱼是有了,但没佐料呢!小孩听后立刻回家,十多分钟后气喘吁吁地跑来,拿给我几个蒜头、几个辣椒、几根葱、几棵芫荽,嘴里喊着,桂科叔叔,佐料有啦!逗得我哈哈大笑。”
李桂科与茄叶村民的关系就这么融洽,村民但凡对他有点好处,他都会记得。
茄叶村到山石屏足有五公里。1981年,洱源县防疫站派李桂科等八人进驻麻风院,对麻风病人做检查整顿,建立病历档案,这事干了整整半年。10月底,其余几人撤离,留下李桂科、杨文彬、朱占山、杨德昌四人,由李桂科负责麻风防治,同时在上茄叶健康区。后来朱占山和杨德昌去大理卫校进修,杨文彬回防疫站上班,留下李桂科在麻风院,一直待到1983年底。
山石屏麻风疗养院的健康区,其实早在1963年就曾在离麻风院六百米的黑潓江东岸建过,是健康人管理疗养院的住所。健康区建好后,却没有人居住,因为没有健康人愿意来这里,至今那里还有遗址。为了改变疗养院没有健康人员管理的状况,县卫生局决定将健康区搬到离麻风院五公里的上茄叶村,由洱源县防疫站皮防科医生轮流居住,便于治疗麻风病人。
1981年10月,洱源县投资两万元,在炼铁乡上茄叶村征地四亩,建设疗养院健康区十一间一百七十六平方米,供医生使用。1981年10月至1982年8月,李桂科、朱占山、杨德昌、杨文彬居住健康区;1982年9月至1983年12月,只有李桂科在此居住;1984至1985年,严云昌、杨云虎、王汉喜、许玉梅几人在这里;1986年,张开武和胡正清在这里值班;从1987年后,都是李桂科在这里值守。2000年,李桂科医生搬进了山石屏麻风疗养院,从此健康区闲置,却留下了李桂科的许多美好记忆。
“那个时候,我们从山石屏回到健康区后,就经常步行到江旁道班去玩,更多的时候是道班的人来找我们,也有炼铁的老师和卫生院的医生。我们会过日子,有茶叶、有开水,还有茶杯,他们来了都是自己动手泡茶。我们去他们那里,连杯热水都喝不上。我们还挂了好些腊肉,有次有个炼铁的老师来,盯着挂在梁上的腊肉直咽口水。我说,你别盯着看,我煮给你们吃。”李桂科呵呵笑道。
提及往事,在别人看来是“待不下去”的环境,对李桂科而言却是津津乐道。
我问李桂科:“为啥别人有的回县城,有的去卫校进修,就留你在麻风院呢?”
李桂科笑笑说:“没办法,我们先后进去的十一个医生,只有我是共产党员。”
关键时刻,还是要靠共产党员来扛,党员,就要把急难险重留给自己,从李桂科的身上,我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。
1980年10月,在三营永胜小学附中当民办教师的李桂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那时,他还没想到要考卫生系统,只是将时间和精力用来教书育人。
李桂科一个人留在麻风院这段时间,也是他最忙的时候,他不仅要给患者做清创手术,还要按时发药,同时还要负责健康区的修建,以便医生休息居住。那时,没有床架、没有桌椅,李桂科便到乔后请木匠师傅来做。有时木匠忙不过来,李桂科也亲自上阵帮忙做木工。健康区光秃秃的,没有绿荫,李桂科便到街上买来树苗,亲自动手栽种。
有人问他:“李医生,你花力气把这里建好,说不定很快你就走了,何必那么费力气?”
李桂科呵呵笑道:“该走的都走掉啦,剩下我咋个走?再说了,即便我走掉,县里还会派医生来,好歹有个住处,让后来的医生安心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