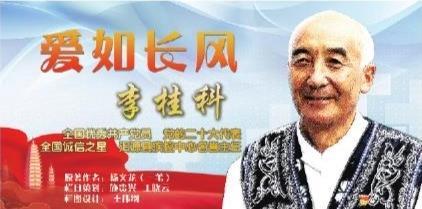山石屏村村民小组长杨晓元说:“当时,村里条件很艰苦,很多患者的病情越来越重,有的身体溃烂,有的缺胳膊断手,有的双目失明。打个不好听的比方,就像人间地狱。那个时候,李医生才二十三岁。当时我们就想,这个小伙子能待得下去吗?他到底会不会治病?他会不会嫌弃我们?说实话,一开始我们也没抱多大希望。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李医生没有畏惧,没有退缩,凭着他的党性和善良,一门心思地帮我们治病,照顾老人,为村里的生产生活忙前忙后。可以说,没有李医生,就没有山石屏的今天!”
那时,山石屏麻风院有八匹马,运送近两百人的食物,显得捉襟见肘。如果是冬春季节的枯水期,马匹可以涉黑潓江到对岸。如果是夏秋季节江水暴涨时,只能绕道三十多公里到上游的潓江吊桥到集市上采购物资,往返得两天,还要在途中住一夜。
对于山石屏疗养院的麻风患者和家属而言,原来到江对岸种地,可以过铁索桥。自从1966年黑潓江发大水冲了铁索桥后,往返麻风院只能靠渡船和溜索。李桂科留在麻风院后,首先想到的是解决交通问题。黑潓江阻隔了麻风患者出村的道路,也阻隔了村外的人们对麻风院的了解。光治好麻风病人的身体是不够的,还要治心,让那些康复者能正常与村外的人交往。
据说,大水冲走的那座铁索桥,就是清末杜文秀起义时,拨两万斤生铁,在潓江上改建的那座神户铁索桥,“炼铁”之名由此而来。不是人们想象中的“铁厂”。清代诗人骆景宙来到炼铁,曾留下诗句:“峻岭嵯峨一涧开,马蹄得得一鞭催。漫言炼城今宵宿,谁识生平炼铁来。”骆景宙曾当过大理知府,当年也曾来过炼铁。炼铁还是茶盐古道上的要冲,当时清末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修铁索桥,也是为了运盐。炼铁下段的长邑村还曾发生过“火烧洋教堂”事件,使得这个小地方令法国人震怒。
李桂科与麻风院的患者们说:“神户铁索桥没有,我们光靠渡船和溜索是不够的,靠那八匹马驮粮食也不够。咱们要修路,以后还要架桥,要使山石屏通向山外,要使疗养院的孩子能到外面去上学。”
李桂科推心置腹的话,感动了麻风疗养院的数百名患者。他们中有老人,也有年轻人,有晚期患者,也有轻症患者。还有患者家属和子女,他们未曾染病,但因为住在山石屏,也被看成与麻风病人无异。听说要修路,大伙都兴奋不已。有组织地拿起工具,到指定地点开挖,好像过节似的。轻症患者和家属每人均分到一截路。有的虽然指关节已经断落,却仍然用剩下的几根指头握紧锄棒,加入挖路的队伍中。有的足底溃疡行走不便,也被人搀扶着到工地上干活。年老体弱者没有力气,就生火烧水,或到集体食堂中帮厨,给大家送饭。
李桂科看着这个奇怪的修路队伍,心里五味杂陈。这群人里,有老人,也有小孩,有男有女,扛着奇形怪状的工具。因为是麻风院,所以连平时用的农具都没法去供销社买。山石屏人全靠自己打铁、自己做家具、自己制造农具、自己磨面、自己养牲口、自己种菜养猪,很多人成了生产能手。比如现在仍健在的余振华老人,就曾做过木匠、铁匠、篾匠,各种生产工具他都能制造。他们的农具也是各具特色。挖路的锄头,厚薄宽窄各异,锄头棒也是有直有弯、有粗有细,有的光滑,有的粗糙。
李桂科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他在心里感慨,这些人是有希望的。中国有句古话,好死不如赖活着!对于绝大多数的麻风病人而言,他们不想死。只要有一线生机,他们不会放弃活着的希望。有些患者,上有老、下有小,即便他们不顾及自己的生死,也要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。想到这些,李桂科眼里放出了光亮,他有信心治好他们的病,也有信心点燃他们生命的心灯。
三公里的车路,从省道平甸公路直达江边。有了这三公里,驮运物资和粮食就省了不少事。麻风院买了辆手扶拖拉机,可以把采购的百货直接拉到江边,再用渡船载到麻风院。李桂科给大家描绘了远景目标,以后还要在黑潓江上修公路桥,把物资直接拉到山石屏。等治好了病,大伙就可以坐上汽车,到县城,到大理、昆明,未来可期。
1981年,洱源县防疫站对麻风病的治疗主要是氨苯砜,与以前黄升东医生治疗方法相同,但很多病人对治愈信心不足,有些人直接拒绝治疗。1983年6月,麻风患者苏晓标病情严重,身体上多处出现溃烂。可他十分固执,他不相信麻风病可以治好,拒绝接受治疗。给他发的药,他总是悄悄扔掉。他的心理也极度脆弱,曾经不止一次试图轻生。李桂科让大家密切关注他的动向。有天夜里,苏晓标不见了,院内的管理人员急忙给李桂科报告。李桂科立即组织了二十几个人去找苏晓标。后来,在黑潓江边的柳林里找到了他。那天夜里,李桂科与他彻夜长谈,与他探讨麻风病的病理、药品的药理,希望他配合治疗。
经过反复做心理疏导,苏晓标转变很快,他开始按时服药,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。经过两年治疗,他的病情大有好转,身体上的溃疡也大多愈合,麻风病已治愈。
苏晓标欣喜若狂,逢人便说:“李医生真是神医!”
李桂科对他说:“我不是神医,是你规范服药的结果。”
其实早在1956年6月,在昆明金马疗养院治愈的康复者黄升东便担任麻风院的医生,并在院内成立了卫生室,在病人中培养了八名卫生员,开展常见病的诊疗,进行常规化验和麻风杆菌检查,组织病理取材送检,用氨苯砜、苯丙砜、氨硫脲、大枫子油等治疗麻风,开展苍耳子、大蒜液治疗麻风的研究。1958年,首批治愈病人八例,到1980年即已治愈八十六例。这在当时,是令人瞩目的成绩。